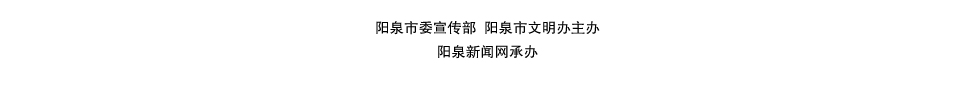流螢染夏,萬物向陽,六月的天氣,總讓人有行至征途中、興致正濃的感覺,正如同熟悉舒平的人對她的評價——“斗志昂揚!” 初見舒平,她干練的短發泛著光澤,發尾利落地收在耳垂下方,深色連衣裙裹著挺拔的肩線……“我是土生土長的陽泉人。”簡單的字詞似帶著某種特殊的力量一般,將人拉回到現實。作為國家一級演員、中國歌劇舞劇院導演,舒平曾參加北京新年音樂會、香港中華藝術節等大型音樂盛會,參與《圖蘭朵》《拉美莫爾露琪亞》《阿依達》《楊貴妃》等多部著名歌劇的演出,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多年來,在外工作的舒平仍然心系家鄉學子,盡己所能為他們提供幫助。 舒平的哥哥是陽泉市文工團的首屆團員,在哥哥的影響與父母的支持下,年僅12歲的舒平進入陽泉市文化藝術學校學習小提琴,成為藝校的首屆學生。 談及在陽泉市文化藝術學校的學習經歷,舒平印象深刻的當數每次學習完理論課程后的練習過程。雖然在進入學校之前,舒平已經有六年的小提琴學習經歷,但由于所在班級是“混齡制”,舒平仍舊跟不上班內其他年長學生的學習進度。 為了更快掌握專業知識,她經常一練就是七八個小時。遇到不會的問題,她就一遍一遍地抱著琴找老師請教;缺少練習曲譜,她就“厚著臉皮”找老師借曲譜書手抄;家里不方便練琴,她就背著琴步行五公里到市工人文化宮練習。為了增強手指靈活性、準確性、協調性,鞏固肌肉記憶,舒平堅持冬天在戶外練琴,“冬天氣溫低,但手指‘運動靈活’的過程就像是手部的負重運動,能夠促進復雜技巧的突破。”舒平坦言。 一勤則天下無難事。空閑時間,她還會跟隨戲曲班、歌舞班的同學一起練習戲曲基本功,久而久之,她在掌握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基礎上,還學習到了不少戲曲功夫,為她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礎。 “在藝校學習的過程中,我不僅收獲了扎實的功底,更鍛造了堅韌不拔的意志品質。這份由內而外的堅韌與專業能力,成為我藝術道路上堅實的內核。”舒平說。 從藝校畢業后,舒平在陽泉一中求學時,遇到了改變她一生的人——張英老師。張老師一句“嗓子可以”,領舒平踏上了學習聲樂的道路。從初中至高中,舒平拿出了在藝校求學時的那股勁兒,她堅持“兩班倒”的學習方式,與同班同學一起學習文化課,同學們放學回家后,她又開始學習聲樂。周末,舒平還會前往北京求學,短短兩天的時間,一半都要耗費在路上。當被問到這樣是否值得時,舒平說,“藝術的界限或許是人為畫的牢籠,我始終相信堅持就會有回報,熱愛可以抵歲月綿長!” 終于,舒平的努力有了回報,高中時,她代表市總工會參加全省調演,被山西省歌劇舞劇院選中并推薦至中央戲劇學院學習。之后,她又考入中國音樂學院進行本科階段的學習并免試保送攻讀研究生。31歲時,舒平終于結束了“學生生涯”,先后在中央歌劇院、中國歌劇舞劇院任職。自2015年起至今,她受邀為北京大學、中國音樂學院、沈陽音樂學院等院校排演《原野》《傷逝》《洪湖赤衛隊》《江姐》等多部歌劇。 “故鄉永遠是我的精神家園,滋養著我成長,故鄉的發展變化也牽動著我的心。”為了幫助陽泉的藝術學子“走出去”見識更廣闊的天地,舒平用現有的資源,為他們“引路搭橋”。在她的努力下,陽泉成為中國歌劇舞劇院藝術考級的承辦單位,為本地學生提供了更多接觸國家一流老師指導的機會。同時,她與陽泉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等院校建立聯系,探索推動“大改乘”和“軍轉空”項目,為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和退伍軍人提供職業培訓與就業機會,還推薦學生前往中央戲劇學院深造,幫助他們考取專業院校。 藝術教育不是流水線加工,而是應該點燃火把、把光傳給下一代。而舒平,就是傳遞光的“使者”,因為經受過學藝道路的艱辛,她愿意把“傘”撐給更多的熱愛藝術的學生,讓千千萬萬個懷有夢想的青少年在逐夢的道路上走得更順暢。“只要條件允許,我都會不遺余力為家鄉學習藝術的學子提供指導。”舒平說,那些傳遞著的“火把”終將化作穿越時空的星光,照亮更多仰望藝術蒼穹的眼睛。張佳雨文/圖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