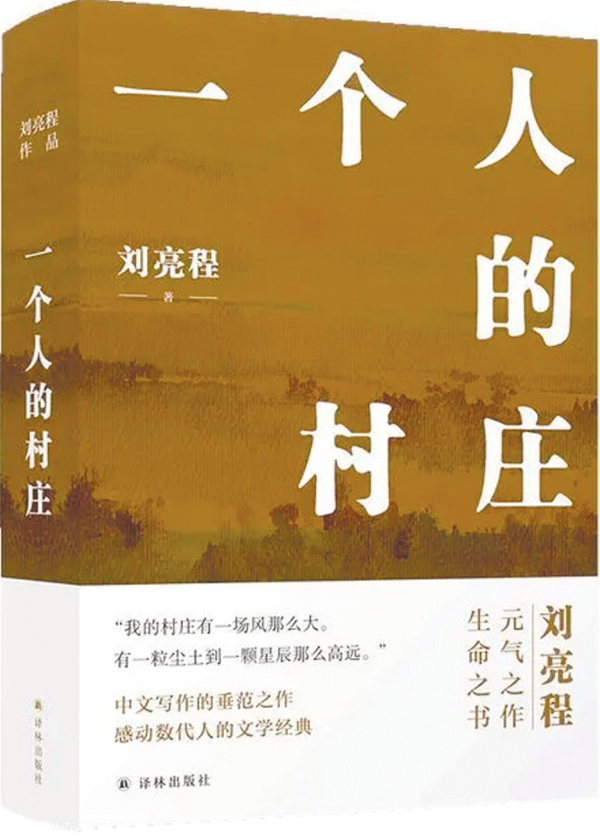
國人的鄉土情結,由來已久。 中年之后,相比較閱歷,對于故鄉的情懷,猶如一顆早已生根發芽的種子,外界看到的,僅僅只是幾片葉,殊不知,這份帶著鄉愁思念的根系,早已在內心深處,盤根錯節,蟄伏許久。誰說風過無痕?時機一到,對于故鄉的眷戀,撲面而來,久久難以釋懷。 費孝通曾經在《鄉土中國》里這樣寫道:“我們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下人,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。我們說鄉下人土氣,雖則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,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。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。鄉下人離不了泥土,因為在鄉下住,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。這樣說來,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。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,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。” 正如先生所言,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,幾千年來,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群始終依賴土地為生,形成了穩定而封閉的社會結構。這種穩定性不僅體現在地理空間上的不流動性,更體現在社會關系、文化習俗和道德觀念等方面的傳承與延續。 無獨有偶,作家劉亮程的《一個人的村莊》之所以能夠引起我的共鳴,恰恰是那種帶著泥土芬芳接地氣的文筆,吸引了我,某種程度上,滋養了我的靈魂。 毋庸置疑,每個作家筆下的故鄉,都是以自己故鄉為背景的書寫,自然而然,故鄉猶如母親,無論如何貧瘠與瘦小,都會在作家心里真實而美好地存在,這就像那句有名的俗語“兒不嫌母丑”一樣的心情。于是,即使故鄉猶如衰老或者逝去的老人,即使故鄉遍地土坷垃,即使故鄉荒蕪而蒼涼,請相信作家的筆力,在他的筆下,故鄉必定是桃花源般的存在,必定是古樸而自然的,必定是那片魂牽夢繞的人間樂園。 于是,劉亮程老師把故鄉的一草一木,一枯一榮,以“鄉村哲學家”的視角來審視;于是,他像莊子那樣隨性而行,拎上一把鐵鍬,在村外的野地上轉悠,看哪兒不順眼就挖兩下。這就是故鄉的包容帶來內心的從容,讀者在他的文字里,一邊大口“呼吸”著來自田間地頭鄉野的氣息,一邊在深沉而質樸的這種收獲中,感受來自內心的安寧,直到,心如止水,波瀾不驚。 坐在黃沙梁的夕陽里,點燃一支煙,讓晚霞,燒得再絢麗一些。 《一個人的村莊》里的孤獨,就像一座沉寂多年的老屋,就像一只在村莊田野里巡回出沒的流浪狗,如同作者,耐心地守候過一只小蟲子的臨終時光。“在永無停息的生命喧嘩中,我看到因為死了一只小蟲而從此沉寂的這片土地。別的蟲子在叫,別的鳥在飛。大地一片片明媚復蘇時,在一只小蟲子的全部感知里,大地暗淡下去。” 而他與他的黃沙梁,如同一位隱者遠離繁華與喧囂,獨守這份孤獨與自在,寂寞與愜意。 于是,他有了這樣的哲思:“很多年前,我們都在的時候,我們開始了等候。那時我們似乎已經知道,日后能夠等候我們的,依舊是靜坐在那些永遠一樣的黃昏里,一動不動的我們自己。”于是,他推開了外出游子的心扉:“故鄉是一個人的羞澀處,也是一個人最大的隱秘。我把故鄉隱藏在身后,單槍匹馬去闖蕩生活。”于是,他在故鄉容不下肉身,他鄉容不下靈魂的釋懷中,用筆尖寫下:“一個人心中的家,并不僅僅是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,而是長年累月在這間房子里度過的生活。盡管這房子低矮陳舊,清貧如洗,但堆滿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黃金般珍貴的生活情節,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擁共享,別人是無法看到的。走進這間房子,你就會馬上意識到:到家了。即使離鄉多年,再次轉世回來,你也不會忘記回這個家的路。”這樣柔情的文字,深夜,我在這段文字中,感同身受,淚眼模糊。 成長,總是教會我們很多,那些平凡生活里的哲學。只是有的人一筆帶過,劉亮程下筆成金: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,我們不能全部看見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,孤獨地過冬。 在《一個人的村莊》里,那些隨處可見的文字稍加組合,帶有鄉土氣息的哲思,就會閃現在我們面前,正如他說:“成長是一個自己不知道的秘密過程,我們不清楚自己已經長成了什么樣子。多少個秋天的收獲之后,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。我從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,并不是草木的道理。我自以為弄懂了它們,其實我弄懂了自己,我不懂它們。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,我們真正要找的,再也找不回來的,是此時此刻的全部生活。” 正如讀者所言,劉亮程《一個人的村莊》與其說是一部散文集,倒不如說這是他為故鄉寫的長歌行。在這些踏實的詩行中,他凝視著眼前的村莊,對自己,又仿佛對所有熱愛故鄉與文字的讀者說: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,干好,人就漸漸出來了。(吳鵬程) | 
